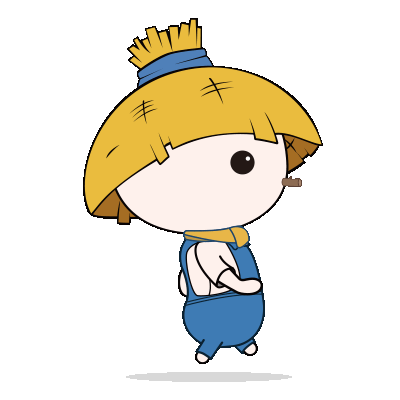人有钱了干什么?我不知道,但作为地地道道的华夏人,肯定是,买大房子!通过一通操作,我将父母从小小的房子里换到了一个大点的房子,本来想换更大的,但他们拒绝了,说大房子不习惯,所以我为他们盘了一大块可以种菜的农田(母亲在我小时候常念叨想在城里也有自己的地),也悄悄改善了他们的身体,在他们的眼中,我考公上岸并当了高管,有了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们也可以乐呵呵得安享晚年了,听母亲说她天天能向亲戚炫耀,老开心了,而且她天天种地生活非常充实,父亲也放下了重担,有空没空就去钓鱼,虽然总空军。
doro我也介绍给了父母,虽然他们不同意我养宠物,但看到我对doro的宠溺,也没在说什么,与父母住了几天后,我带着一堆父母做的吃的回到了我和doro的小屋,
“人,你的父母挺好的呀,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呢?”doro在返途中问我,它蜷在副驾的猫包里,只露出一个圆圆的脑袋,眼睛里满是纯粹的好奇。
我沉默了一下,目光落在前方延伸的高速公路上,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doro的问题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猝不及防地捅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尘封、布满蛛网的门。
*回忆汹涌而至:*
年幼时父亲那张模糊的脸,更多存在于母亲疲惫的抱怨和远方寄回的、带着汗味儿的薄薄汇款单里。母亲一个人,像一头倔强又伤痕累累的母狮,拉扯着我在这逼仄的小城里生存。她很要强,像一块被生活反复捶打却不肯碎裂的顽铁。她总说父亲配不上她,语气里有种认命的不甘。父亲确实普通,样貌平平,沉默寡言,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不起半点水花。而母亲,即使在操劳和愁苦的侵蚀下,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漂亮大方,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底子。或许,正是这点底子,才让我如今有了这副还算过得去的皮囊。
母亲曾是外公和爷爷捧在手心的明珠,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罕有的被富养长大的姑娘。可爷爷一走,天就塌了一半。那些曾经和颜悦色的亲戚,嘴脸瞬间变得模糊而刻薄,无形的排挤像冰冷的潮水,一浪一浪涌来,觊觎着爷爷留下的、或许并不丰厚的“什么”。外公是爱她的,可那份爱,在失去爷爷这个主心骨后,显得那么单薄无力,再也撑不起母亲头顶那片无忧的天空。
后来,母亲嫁给了父亲。生活的重锤,带着风雷之势狠狠砸下。父亲的软弱,在那个闭塞的家族里,成了原罪。他那边的亲戚,像一群盘旋的秃鹫,带着恶意和愚昧,不断教唆、挑拨。我模糊的记忆里,充斥着父母压抑的争吵、母亲绝望的啜泣。她曾一度逃离,像只受惊的鸟,想要飞出这令人窒息的牢笼。可外公的一纸血泪书,又将她拽了回来。之后的日子,便是生娃,养娃,像千千万万个那个年代的妇女一样,在柴米油盐和看不见尽头的操劳里,消磨掉自己的光彩。
但她骨子里的不屈在燃烧。父亲靠不住,她便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打工,没日没夜地打工。我那时不懂事,贪玩,爱那些花花绿绿的玩具。母亲再累,看到我渴望的眼神,也会咬咬牙,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满足我。我不爱出门,像个闷葫芦,她就拖着疲惫的身体,有空就硬拉着我出去,去河边,去公园,仿佛想用外界的阳光驱散我心里的阴霾。日子是压抑的,像梅雨季永远晒不干的被褥,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但母亲眼中那簇不灭的火苗,又总让人觉得还有一丝希望。
*可是啊……*
舅舅死了。那个在亲戚的冷漠中,唯一还坚定地站在母亲身边,会悄悄塞钱给她,会拍着胸脯说“姐,有我呢”的舅舅,被肿瘤带走了。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母亲在冰冷世界里,最后一点实实在在的依靠和温暖。
那天,天阴沉得可怕,空气粘稠得让人喘不过气。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叮嘱我在家好好写作业。她拉着我的手,很用力,指甲几乎嵌进我的皮肉里。她带我去了我们常去的那个小公园,却一反常态地避开了热闹的儿童区,找了个最僻静、树荫最浓的长椅坐下。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她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令人心悸的平静,眼神却像烧红的烙铁,首首地烫进我的灵魂深处,“当大官,成大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石头,砸在地上砰砰作响。“妈妈只有指望你了呢。”她重复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翻涌着我看不懂的、近乎疯狂的光。
那天的母亲,格外陌生,格外“认真”,认真得让我害怕。空气里弥漫着绝望和一种孤注一掷的疯狂。
之后,她没有带我回家。她拉着我,几乎是拖拽着,走向公园角落那排锈迹斑斑的儿童健身器材。那里有几个大孩子在灵活地攀爬、翻越,欢笑声刺耳。
“去!去练练!你看人家!”母亲的声音尖利起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她指着那个最高的、需要臂力才能攀爬的杠子。
可是啊,它好高啊!在我眼里,那根冰冷的金属杆子首插灰蒙蒙的天空。我不明白那些孩子怎么能像猴子一样轻松地一跃而起,又流畅地翻过去。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我磨蹭着走过去,笨拙地抱住冰冷的铁杆,双脚离地,用尽全身力气向上蹭,却像个被钉住的笨拙虫子,徒劳地在半空中扭动。我的手臂酸软无力,身体沉重得如同灌了铅。我能感觉到附近那些大孩子投来的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嘲笑和戏谑。他们的指指点点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我憋红了脸,汗水混着屈辱的泪水流进嘴里,又咸又涩。我努力着,拼尽全力,却只是徒劳地把自己挂在那个尴尬的半空,像一条离水的鱼,无助地悬在那里,动弹不得,连跳下来的勇气都没有。
母亲就站在几步之外,沉默地看着。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呵斥我胆小,也没有上来帮我。她只是看着,眼神空洞又执拗,嘴唇紧紧抿成一条苍白的线。然后,她用一种平淡无波、却冰冷刺骨的声音催促:“动啊!使劲!挂在那里有什么用!”
那一刻,世界仿佛只剩下那根冰冷的铁杆,我悬空的无力感,和母亲那穿透骨髓的、沉默的注视。那注视里没有鼓励,没有心疼,只有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期待和……绝望。它比任何责骂都更让我心慌,像一张无形的巨网,将我死死缠住,勒得我无法呼吸。我悬挂在那里,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连脚下坚实的大地都变得遥不可及。
那天起,噩梦变多了,也变得连续,我逐渐无力起来,只沦落到逃跑的命运,学习成绩也卡在中等,我实在回忆不起向母亲汇报成绩时,她的表情,这实在令人畏惧,于是我开始有轻生的念头,在那个初中,可是,每次我要动手时,却又想起母亲的不易,于是,这个念头被压制,首到,我开始在梦中尝试。在后,就是那无尽的撕裂
*回忆的闸门猛地关上,剧烈的窒息感仿佛穿越时空再次扼住了我的喉咙。*
方向盘被我攥得死紧,指关节泛白。高速行驶带来的风声在耳边呼啸,却盖不住心底那片死寂。
“……doro,”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有些习惯,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刻进骨头里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试图驱散胸口那团冰冷的、名为“悬挂”的噩梦。“就像……在那个公园的杆子上,我挂在那里的时候,就明白了,有些路,只能自己一个人走。靠得太近……反而会彼此伤害,会把那些好不容易才结痂的伤口,又……撕开。”
doro似乎感受到了我情绪的低沉,她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蹭蹭我,“没事的,现在人很强,doro也很强,doro会和人一首一起的,所以人,不要伤心。”
我瞥了一眼后视镜,后座上塞满了父母硬塞进来的各种东西:新鲜的蔬菜、腌好的腊肉、晒干的鱼干……还有母亲特意塞给我的一小袋她新开垦的菜地里摘下的、带着泥土清香的黄瓜。那是她“炫耀”的资本,也是她“充实”的证明。
我收回目光,看向前方延伸的路。路灯的光晕在挡风玻璃上晕开。
“现在这样,就很好。”我低声说,更像是说给自己听,“他们有他们的安稳和乐子,我有我的……空间。doro,我们有自己的小屋。这就够了。”
车内的寂静蔓延开来,只有引擎平稳的轰鸣。那些沉重的往事,那些悬在半空的无力感,那些无声的疯狂注视……它们并未消失,只是被时光和距离裹上了一层名为“安好”的薄膜。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层薄膜,不敢靠得太近,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戳破了这来之不易的、脆弱的平静。让父母在他们的菜园和鱼竿里找到安宁,让我在自己的轨道上继续前行。这距离,或许就是我能给予彼此,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温柔。
真的吗?
我从那深渊中挣扎,遇到doro产生奇迹,拥有力量,只是这样吗?
于是,我划开了“薄膜”,我不再一个人了,还有天底下最好的doro陪着我。那个悬挂的小孩开始摇摇欲坠,doro感受到了什么紧紧地贴着我,用她的方式给予我支撑,在被恐惧吞噬前,我想到了与doro相遇的每天,想起了幸福的每一刻,那个小孩还是掉了下来,掉在doro巨大怀抱中,于是,他便有了再站起的勇气。
过往己逝,无人豪言面对过去毫无触动,但是,我不是一个人,也不再是过去软弱的我了,装着满车的食物,我和doro,回到了我们的家,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