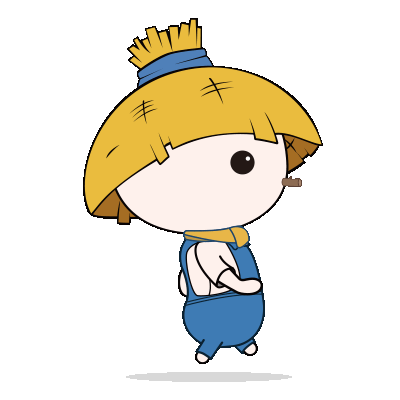第一章 血沁蟾鸣我永远记得那个梅雨季的黄昏,拆迁工地的泥浆里浮出第一只眼睛。
当塔吊铁爪掀开老石库门最后一片屋瓦时,暗青色的天空突然下起酸雨。混凝土碎块在泥浆里咕嘟冒泡,刺鼻的硫磺味中,我瞥见基坑裂缝里闪过一抹铜绿——那是只巴掌大的青铜蟾蜍,眼窝里镶着两粒血珀。
"别动!"
陈师傅的暴喝震得我耳膜生疼。老工程师踉跄着冲下基坑,安全帽被狂风吹落,露出左额狰狞的烧伤疤痕。他颤抖的手悬在青铜蟾蜍上方三寸,浑浊的眼珠倒映着暗红纹路:"血沁入骨,大凶之兆..."
话音未落,基坑突然传来蛙鸣。不是夏夜荷塘的清亮叫声,而是千百只喉咙被割开的嘶哑呜咽。泥浆翻涌间,三十七个工人齐刷刷仰面倒下,他们的工装裤诡异地鼓起,像有无数活物在布料下游窜。
"快走!"陈师傅拽着我冲向临时板房。身后传来混凝土崩裂的巨响,我回头时正看见塔吊司机老王飘在半空,他的肚皮裂开血口,钻出密密麻麻的透明蝌蚪,那些半凝固的胚胎在雨幕中舒展西肢,转眼长出带蹼的手掌。
板房里的《上海市政工程年鉴》摊开在1951年9月。泛黄照片里,戴着圆框眼镜的青年站在如今的拆迁地块,身后是正在浇筑的巨型混凝土方桩。陈师傅的食指重重戳在照片边缘——青年脚边的青铜棺椁纹样,与我捡到的蟾蜍如出一辙。
"当年这里不是工地,是刑场。"老人摘下老花镜,疤痕在台灯下泛着青光,"七个戌时出生的犯人被活埋在七丈深的桩基里,浇灌的混凝土掺着黑驴蹄子粉。"
窗外传来指甲抓挠铁皮的声音。陈师傅突然掐住我的虎口,剧痛中我发现自己掌心浮现出北斗七星状的红斑。老人从贴身口袋掏出块怀表,玻璃表面下不是指针,而是转动的阴阳鱼:"子午相交,阴门洞开。现在开始,我说你记——"
怀表突然迸出裂响,十二个时辰刻度渗出黑血。板房西壁浮现水渍,渐渐聚成民国女子的轮廓,她脖颈处碗口大的伤疤里爬出蛞蝓,落地竟变成金眼蟾蜍。
"走!去城隍庙找..."陈师傅将我推出后窗的瞬间,板房轰然坍塌。我摔在泥水里,看着老人被无数粘稠的触手拖入地缝,他最后抛来的铜钥匙划破我掌心,血珠滴在青铜蟾蜍背部的铭文上,那些虫鸟篆突然睁开猩红的眼睛。
子时的城隍庙地宫寒气刺骨。我举着手机照明,青铜蟾蜍在祭坛凹槽里疯狂震颤。当钥匙插入第七块地砖的锁孔时,整座地宫突然下沉,露出隐藏的冰窖。
十八根汉白玉柱环绕的冰棺里,躺着的竟是个现代装束的少女。她心口插着桃木钉,手腕系着和陈师傅同款的怀表。冰棺侧面蚀刻着《特殊事务处理条例》第13条:"凡建国后擅修人形者,立诛三魂。"
手机突然收到推送:"静安府工地塌方事故致38人失踪"。配图里戴着金丝眼镜的救援队长,分明是1951年老照片里的青年勘察员。我颤抖着点开详情页,热评第一条是ID"第七档案室-周"的留言:"镇物移位,子时三刻封门。"
冰棺在这时迸出裂响。少女尸体睁开金瞳,腹腔内传来蛙鸣,无数冰渣从她七窍涌出,在空中凝成半透明的人形。那东西抚摸着我的脸颊,指尖寒气在皮肤上蚀刻出北斗纹路:"好孩子,该把命格还给我们了..."
晨光刺破云层时,我握着陈师傅的桃木剑跪在废墟上。手机循环播放周明远的语音:"林小姐,您继承的'戍午破军命'是最后一道锁,请立即撤离..."但我知道自己逃不掉了——掌心七星斑己蔓延到肘部,每道红斑里都嵌着粒金蟾眼珠。
拆迁办的人赶来时,我正把青铜蟾蜍按进心口。血肉交融的剧痛中,我看到1949年的雨夜:七个青年在混凝土桩基前割开手腕,他们的血在青铜棺上画出北斗阵图;1951年的镇压现场,陈师傅还是孩童模样,被他父亲亲手推进注满符水的桩孔;而此刻我的脊椎正在变异,十八根骨刺穿透工装服,在朝阳下泛着汉白玉的光泽。
"最新消息!静安府工地惊现明代古墓!"记者们的镜头对准基坑下的青铜棺椁。我蜷缩在救护车阴影里,看着周明远指挥工人覆盖防水布。他西装内袋露出的怀表链子上,坠着颗和陈师傅同款的金蟾眼珠。
梅雨又至。我摸着后颈新生的鳞片,在手机记事本里写下最后遗言:"当你们看到这段文字时,第七根镇魂柱己经..."突然响起的消息提示打断输入,业主群里正在转发寻人启事——失踪的塔吊司机老王今晨出现在苏州河畔,监控画面里,他正蹲在防汛墙上产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