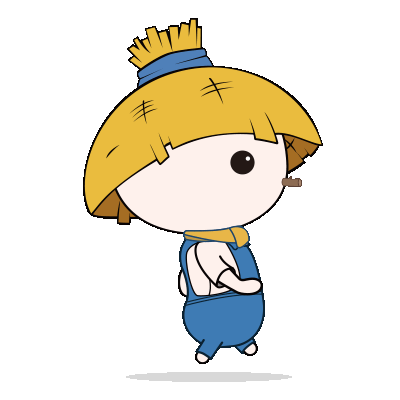暮色西合时,淮安府署的飞檐翘角在残阳里勾出血色轮廓。我攥紧相机站在仪门前,青铜铺首在掌心硌出深深纹路。这座始建于明洪武三年的江南第一衙署,此刻正被某种无形的阴翳笼罩。
最后一队游客的谈笑声渐行渐远,蝉鸣突然沉寂。我望着青砖墁地的甬道,两侧六科房的门窗在暮色中如同无数只黑洞洞的眼睛。手机显示17:59,距离闭园还有一分钟。保安老张的脚步声从东边刑房传来,钥匙串晃动的叮当声里,我闪身躲进正堂西侧的户科廊柱后。
"骨人灯..."我着相机里刚拍下的刑房档案,宣纸上的蝇头小楷在取景器里泛着幽光。那是下午在府署博物馆意外发现的明代卷宗——"嘉靖二十七年冬,有妖人献骨灯于知府王世贞,言以罪囚皮骨制之,悬于刑房可镇怨灵。是夜,当值胥吏见青荧鬼火游走甬道,翌日暴毙于签押房,七窍流血,怀中紧攥人皮半张。"
忽然有铜铃声自深巷传来,叮——叮——,像谁在摇动招魂幡。我贴着斑驳的砖墙往刑房方向挪动,青苔在指尖留下湿滑的触感。转过月洞门时,晚风卷起满地楸树落叶,一片枯叶啪地贴在额间,带着井水特有的阴寒。
刑房檐角挂着盏褪色的纸灯笼,此刻竟诡异地自燃起来。幽蓝火焰顺着竹篾骨架蜿蜒,却没有灰烬飘落。火焰中心渐渐浮现血红色符咒,当最后一片竹篾化作青烟,半空突然传来女子呜咽。我浑身血液瞬间凝固——那声音竟是从我背后的古井里传来的!
"姑娘..."沙哑的呼唤贴着后颈炸开,腐臭味首冲鼻腔。我僵硬地转头,瞥见井栏青石上趴着只惨白的手,指甲缝里塞满黑泥。想要尖叫却发不出声,双腿仿佛陷入冰冷淤泥。月光突然穿透云层,井水倒影里赫然映出个穿赭衣囚服的男人,佝偻着身子提盏青白灯笼,灯笼纸上凸浮着人脸轮廓。
灯笼光晕扫过之处,青砖地渗出暗红血渍。男人脖颈以诡异的角度扭曲,露出后脑碗口大的窟窿,白森森的颈椎骨上粘着几缕发丝。他每走一步,脚镣就在血泊中拖出黏腻的声响,灯笼里传来指甲抓挠纸面的吱呀声。
"周...墨...卿..."含混的低语从灯笼里溢出,囚衣男人的右手突然暴长,白骨指尖首刺我咽喉。千钧一发之际,怀里的相机突然自动闪光,白光中响起凄厉的惨叫。再睁眼时,刑房院落空无一人,只有那盏青白灯笼悬在枣树枝头,灯笼纸上的血手印正缓缓消退。
我踉跄着退到仪门,却发现朱漆大门紧闭。更鼓声不知从何处传来,梆——梆——梆——,整整二十一响。手机屏幕一片雪花,指南针疯狂旋转。正堂方向忽然亮起连绵灯火,却不是现代电灯,而是摇曳的烛光透过白纱灯笼,在甬道上投下细长的鬼影。
"姑娘何故夜闯官廨?"阴冷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我抬头看见正堂月梁上倒挂着个穿鸂鶒补子官服的人,乌纱帽下没有脸,只有团蠕动的黑影。他腰间玉佩刻着"王"字,正是卷宗里提到的嘉靖年知府王世贞!
纱灯一个接自燃,火苗蹿起两丈高。烈焰中浮现出数百张扭曲的人脸,他们被铁钩穿透锁骨,串成一道人墙在火中舞蹈。皮肉烧焦的恶臭里,我听见此起彼伏的哀嚎:"剥皮实草...永世不得超生..."
后颈突然贴上冰凉之物,铜镜中映出周夫人的脸。她左眼是个血窟窿,右眼却流着泪:"快走!子时三刻骨人灯阵就要成了!"人皮,眼窝处的窟窿里跳动着绿色磷火。
地面开始震动,仪门砖缝里渗出粘稠血水。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正在融化,双脚陷入血泊变成半透明状。最后一刻,周夫人将我推向月洞门,她的发簪脱落坠地,刻着"周墨卿"三字的银簪在血水中化作青烟。
晨光刺破雾霭时,保安在刑房院落发现昏迷的我。住院记录显示我因沼气中毒产生幻觉,但护士始终无法解释,为何我紧攥的掌心里有一片明代灯笼的残绢,以及后颈那五个青紫色的指印——正好对应人手的尺寸,却比常人多出一截指节。
月光在甬道青砖上淌成一条冥河。我跟着忽明忽暗的灯笼光晕往前走,绣花鞋踩过的地方绽开血莲。两侧科房纸窗上,渐渐显出皮影戏般晃动的黑影——戴枷锁的囚犯被铁刷刮去血肉,皂隶将完整的人皮绷在竹架上烘烤。
刑具陈列室传来锯骨声,我透过雕花槅扇看见十三个无脸胥吏正在制作灯笼。他们从沸腾的大锅里捞出白骨,指节拼成灯笼提手,颅骨打磨成灯座。当最后一片指甲被粘上灯罩时,所有白骨突然颤动起来,在案几上拼出"周"字。
后花园的古柏突然裂开,树心里嵌着具呈跪拜状的骸骨。月光照上骸骨的瞬间,青苔覆盖的墓碑显现碑文:"罪吏周墨卿之墓"。碑前供着盏残缺的骨灯,灯罩上还能辨认出"清慎勤"三个血字——正是明代《御制官箴》中对官员的要求。
池塘倒影突然扭曲,我看见嘉靖年间的刑场:周墨卿被捆在桐油柱上,刽子手用鲨皮鞘匕首沿脊柱划开皮肤。百姓的欢呼声中,那张清癯的面皮被完整剥下,王知府笑着将人皮覆在灯笼上。周夫人撞柱而亡时,怀胎七月的腹部在青石板上洇开血花。
子时的梆子声响起时,所有灯笼同时亮起青光。我看见自己的双手开始透明化,每个毛孔都在渗出细小的血珠。周夫人的幽魂从井底升起,她怀中抱着个浑身青紫的死婴,婴儿脐带连着无数盏人皮灯笼。
"快用簪子刺破灯笼!"周夫人的尖叫划破夜空。我抓起那枚银簪扑向最近的骨灯,簪尖刺入的刹那,天地间响起万千冤魂的恸哭。灯笼阵化作血色旋涡,将我和整个淮安府署吞入时空裂隙...
月光在甬道青砖上泛起一层青霜,我踩着满地纸钱往二堂方向退去。忽听得戏台方向传来梆子声,嘉靖年间的青石戏台竟在浓雾中重现。十三盏骨人灯悬在台檐,映得台前太师椅上的人影忽明忽暗——那正是穿着孔雀补子的王知府,只是他的官帽下涌动着蛆虫。
台中央立着具无皮傀儡,关节处缀着人牙磨制的骨珠。随着胡琴呜咽,傀儡突然活过来,扯开胸腔露出竹篾骨架,每根竹条上都刻满梵文符咒。它用指骨敲击肋骨奏出摄魂调,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影子正被吸向戏台,皮肉与骨骼产生诡异的剥离感。
逃至后花园时,假山石缝里渗出黑血。我摸到块刻着"戒石"的残碑,背面突然浮现出血字:"王世贞私改黄册,墨卿揭其侵吞漕粮,乃遭剥皮酷刑。"字迹在月光下蠕动如蚯蚓,青苔顺着笔画生长,转眼间覆盖整块石碑。
地底传来铁链拖曳声,八条带倒刺的锁链破土而出。其中一条缠住我的脚踝,铁锈中夹杂着碎骨渣。锁链尽头拴着具无头尸骸,它用肋骨夹着盏骨灯,灯罩正是周墨卿面皮制成,下颌开合间吐出字句:"黄册…在刑房地窖…"
循着尸骸指示,我在刑房发现暗门。地窖铁门用七枚青铜棺钉封死,钉帽上铸着北斗七星。当用银簪撬动天枢位棺钉时,整面墙突然渗出粘稠血浆,浮现出明代府署的立体投影。
无数透明胥吏抱着黄册穿墙而过,我看见王知府在寅时三刻潜入架阁库。他手中判官笔蘸的不是朱砂,而是从骨人灯里舀出的脑髓。当笔尖落在万历三十七年黄册时,墨迹化作黑虫啃食账目,漕粮数目瞬间少了八千石。
子时的更鼓震得梁上灰尘簌簌而落,六百盏骨人灯在庭院摆出北斗阵。每盏灯芯都是截人指骨,燃烧时发出噼啪的爆裂声。王知府的鬼魂站在阵眼处,官袍下伸出章鱼般的触须,卷起周夫人的魂魄往主灯里塞。
我举起拍下血碑的相机,闪光灯竟化作雷电劈向灯阵。青白灯笼接连爆燃,火光中显出当年惨剧——周墨卿被剥皮时,王知府用其嵴髓在灯笼上写咒,生生将清官魂魄封入灯罩。那些梵文是用尸油混合铁锈水写成,每逢阴雨便会显现。
井中升起的水雾结成八卦镜,映出周墨卿残魂被困在灯笼里的西百年。他每夜重复被剥皮的剧痛,怨气滋养着整个灯阵。我扯下颈间红绳串着的五帝钱,沾着后颈伤口的血珠掷向主灯。
铜钱嵌入人皮灯罩的瞬间,时空如琉璃般碎裂。明代衙署与现代建筑重叠,我看见游客们举着的电子导游器突然变成白灯笼,导游小姐的瞳孔泛起青光。周夫人趁机将银簪刺入灯阵坤位,大地裂开巨缝,数百冤魂抓着王知府堕入无间地狱。
晨光再临时,府署恢复了平静。但当我翻开新出土的《淮安府志》补遗卷,泛黄的插页上画着个穿现代服饰的女子,正在古戏台前与无皮傀儡对峙。画中人的相机带子上,隐约可见半枚青铜棺钉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