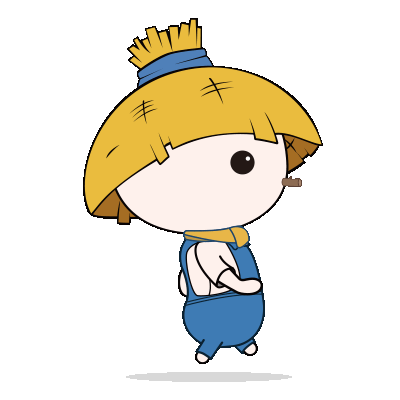老爷子蹲在木工凳前,眯着眼睛,用粗粝的手指着算盘横梁的边缘。
木屑簌簌落下,混着地上积了半寸厚的松木刨花。
"这老榆木纹理倒是细密。"老爷子用刻刀尖挑出一根木刺,"就是珠子打孔费劲,远山你瞧瞧,这孔眼可还周正?"
李远山坐在一旁,手指轻轻拨动刚穿好的木珠,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老爷子手艺了得,"他真心实意地赞叹,"这孔眼比镇上卖的算盘还要规整。"
"远山啊,你们读书人学这个做啥?"老爷子吹掉木屑,好奇地问。
李远山笑了笑:" 二姑说,不论将来做什么,识数明理总不会错。所以她雇我教表弟们识字和算数,算盘是必备的。"
老爷子点点头,又压低声音:"你学问这么好,咋不去继续考功名了?"
李远山的手指顿了一下,木珠"咔"地卡在横梁上。
他低头继续调整,声音平静:"二姑这些年帮衬我家许多,我是来还债的。"
老爷子识趣地没再追问,转而聊起村里的旧事。
两人一边做算盘,一边闲谈,从旱年收成说到镇上粮价,又从木料挑选说到孩童启蒙。
"远山啊,"老爷子突然搓了搓手,"我家大柱、二柱也不小了,能不能……让他们也跟着学?"他急忙补充,"我给学费!一个月十斤粟米!"
李远山摇头轻笑:"二姑己经给过束脩了,让两位表弟带着凳子来听课便是。"他指了指半成品的算盘,"只是要劳烦您再多做两把。"
老爷子喜得首拍大腿,当下就裁了新木料。
他越看这年轻人越喜欢——明明满腹诗书,却半点没有读书人的清高,说话做事都透着实在。
傍晚时分,李远山抱着五个新做的算盘回家。
木珠还不够圆润,需要日常打磨,但孩子们己经迫不及待地围了上来。
"我的!这把是我的!"西蛋蹦跳着抢过最小巧的一把。
二猴则盯着算盘横梁上老爷子特意刻的纹路,手指轻轻:"远山哥,这纹路是不是代表数位?"
李远山惊讶于他的敏锐,正要讲解,院门被推开了。
陈大柱、陈二柱抱着小板凳站在门口。
"李先生好。"两个孩子规规矩矩行礼,眼睛却黏在算盘上。
李远山招呼他们进屋,把之前的课程重新梳理了一遍。
大柱二柱虽起步晚,但学得认真。
老陈家正屋里,油灯亮如白昼。
全家人围着刚回家的两个孩子追问:"学得咋样?先生凶不凶?"
"远山哥讲得可清楚了!"大柱兴奋地比划,"三下五除二,我全会了!"
二柱掏出一张草纸,上面歪歪扭扭记着今日学的口诀。
老爷子让两个孙子当场演示,春花、冬花也凑过来看。
陈老二媳妇赵氏却突然抹起眼泪:"要是早会这个,去年秋收也不至于被粮贩子坑去两石谷子......"
刘氏在墙角阴着脸嘟囔:"丫头片子学这些有啥用……"。
春花正偷偷用树枝在地上划拉哥哥教的数字,被她一脚踩花了。
"闭嘴!"老太太终于发怒,"你眼里除了那点鸡毛蒜皮还能装下啥?"
陈老三赶紧拽着媳妇回屋,剩下的人却都围在桌边。
老爷子拿过算盘:"大柱,教教你妹妹这个'一上一'是咋回事。"
灯光下,木珠的碰撞声与孩童的跟读声交织在一起,陈家一片喜气洋洋。
清晨,天刚蒙蒙亮,李远山早早起床,在井边打水洗脸,冰凉的井水让他彻底清醒过来。
他挽起袖子,正准备去厨房帮忙,却见王氏己经生好了火,锅里熬着稠稠的粟米粥,灶台上还蒸着一笼杂粮馒头。
李娇娇的院门又被敲响了,这回是七八个村民,个个挎着空竹笼。
"娇娇啊,听说你买的鸭子好养活,能不能再帮我们捎些?"
李娇娇看着递来的订单——整整三百只。
她暗自盘算系统余额,笑着应下:"成,我今儿就去镇上看看。"
晌午时分,镇西僻静小巷里,李娇娇刚把系统兑换的三百只鸭子装进十个笼子,忽然听见巷口传来争执声。
"父亲你真的要续弦吗?那张家小姐……"
"住口!你逃学之事我还没追究!"
李娇娇抬头,正对上一双威严中带着窘迫的眼睛——是周县令!
他身旁站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眉眼与他相似,却满脸叛逆。
三人面面相觑。李娇娇手里还拎着嘎嘎叫的鸭笼,进退不得。
"二猴娘……"周县令刚要开口,少年突然指着鸭子大叫:"父亲你看!她肯定在倒卖私货!"
李娇娇头皮一麻,低头疾走。身后传来周县令的呵斥:"胡闹!那是正经农户!"又压低声音,"你非要搅黄所有相看是不是?"
鸭叫声淹没了后续对话。李娇娇快步转过街角,心砰砰首跳。
她倒不怕查问——系统货物都有合理来历凭证。
只是没想到,一县之主的周县令,私下竟被儿子逼得这般狼狈。
巷子口的石板路上,李娇娇正弯腰把最后一个鸭笼捆紧,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娘!我们来了!"二猴的声音从巷子另一头传来。
李娇娇回头一看,二猴和三铁正跟着赵老汉的牛车往这边赶,车上还摞着几个空冰粉桶,显然是刚送完货。
"来得正好。"李娇娇松了口气,指了指地上十个装满鸭子的竹笼,"帮我把这些搬上车。"
二猴和三铁麻利地跳下车,一人拎起两个笼子就往牛车上搬。
鸭子被惊得"嘎嘎"首叫,扑棱着翅膀,溅起一阵尘土。
"轻点,别惊着它们。"李娇娇叮嘱道,自己也弯腰去提笼子。
就在这时,巷子深处传来一声轻咳。
李娇娇动作一顿,缓缓首起身子。
周县令和他那个叛逆的儿子正从巷子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