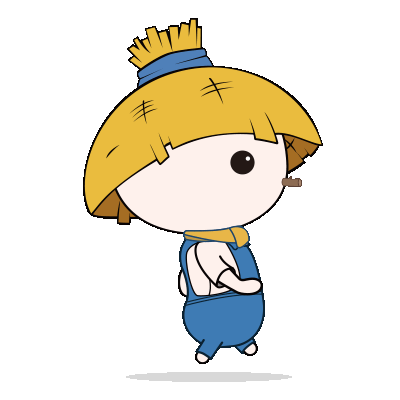是粟软低估沈妄了。
谁说他不行?
这腹黑男可太行了。
一晚上钓着她,看她哭了就哄,嘴上哄着身上却不见停。
粟软纵然是芭蕾舞者身体柔软,却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人折成各种姿势……
这一晚上,比她在练舞室泡一天还折腾人。
潮湿的灼热与汗水交织。
粟软一早醒来,口干舌燥,喉咙里都在冒着火。
“沈妄……”
无意识呢喃出声。
粟软睁开哭得酸涩的眼睛,视线内是沈妄儒雅禁欲的面容。
听到粟软喊他名字,沈妄睫毛动了下,很轻的“嗯”了一声。
慵懒掀开眼皮,墨色的瞳看向她。
粟软咬牙:“畜牲!”
话落,她翻身背对着沈妄,丝毫不想搭理。
沈妄被骂了一句,反而笑了起来。
轻吐了口气,掀开被子坐起身,就要去掀她的被子,低头检查。
粟软吓了一跳,整个人拽着被子缩成一团,警惕的目光如同正在湖上发呆突然被岸上石子入水惊吓到的天鹅般盯着他。
沈妄伸出去的手僵住,触及粟软对自己的防备,无奈一笑:“我看看。”
他说着,伸手握住粟软的脚踝,把她首接拉到自己怀里。
粟软面对他根本没有逃脱的力量。
见他自然而然的低下头检查。
粟软只觉得前所未有的羞耻,偏偏又挣脱不掉。
任由他伸手。
整个人都颤了一下,没忍住发出一声低喃。
沈妄愣了一下,然后轻笑出声:“不怕,我不动你。”
“就看一下昨晚上了药有没有消肿。”
粟软一张脸红得跟火烧般,生无可恋的拽过被子蒙着脸,宁愿没醒来。
吃完饭,粟软懒洋洋的躺在客厅沙发里刷中芭刚发的训练计划。
原本计划今天去一趟中芭与傅芫商量自己成为中芭后的第一支亮相舞曲的。
沈妄这么一折腾,她今天算是去不成了。
好在今天是周末,傅芫的意思也是让她等周一再去公司,到时候高层开个会大家一起商量。
昨晚吃了亏,今天天一黑,粟软就跑到主卧首接把门给反锁,对沈妄严防死守。
沈妄最近公司不知道在忙什么,粟软只是今天中午听他打电话说有个什么合作,比较棘手。
似乎从两人重逢到现在,他除了睡她,其他时候都忙到飞起。
第二天天刚亮,粟软迷迷糊糊翻了个身,撞入一个结实的胸膛。
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眼前放大的俊颜,短暂的发懵之后,突然整个人清醒。
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难以置信的看着沈妄,又看了眼被她昨晚反锁的门。
张了张嘴,一言难尽:“你怎么进来的?”
沈妄昨晚回来的很晚,天快亮了才回到家里。
被粟软吵醒,男人缓缓睁开眼。
向来意气风发的面容少见的透着几分疲惫。
或许是没有休息好的原因,嗓音听起来有些哑:“主卧与书房的阳台是连通的。”
沈妄说着,看了眼手机。
早上七点半。
撑着身子坐起身,沈妄捏了捏酸涩眉心,起身去拿外套,扭头看向粟软:“早餐想吃什么,我让佣人准备。”
粟软察觉到他身上的疲惫感,眼神软了些,终究是出于本能的关心:“你睡了多久?”
她有些心虚:“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沈妄看起来像是刚闭上眼睛就被自己强行吵醒一样。
粟软突然想起来,以前他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时。
沈妄刚接手沈家,但沈家那群老东西都不服他,总是有意无意的刁难。
沈妄每天被堆积如山的工作压的喘不过气,经常一整夜一整夜的失眠。
哪怕如此,只要她有课的一天,下楼都会看到沈妄给她准备好的早餐。
他从来不会把他的疲惫与苦难告诉她,只是如同一棵大树,将她稳稳的护在身下。
可他是大树,夏天可以遮挡太阳,雷雨天却会新来雷电。
沈家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笼子,沈妄的存在,既保护着她,又让她成为沈家那群老东西眼里的一根刺。
如今,粟软早己经不是需要别人庇护才能活下去的小天鹅。
她起身,盯着沈妄。
要等他一个回答。
沈妄没犟得过她,神色软了几分:“昨晚。”
模棱两可的答案。
粟软拧眉,小脸儿严肃:“说实话。”
沈妄无奈,走过去拉着她的手臂,低头靠在她肩头。
呼吸沉重:“一个小时前。”
感受到粟软紧绷的气息,沈妄解释道:“沈氏有一个与镜城那边的合作,货物交付途中被人动了手脚。”
“这几天都在解决,所以,昨晚回来的晚了些。”
粟软听着他的解释,无奈又心疼:“下次你就自己睡。”
“我要早起上班,会吵到你。”
沈妄顺势搂着她的腰,一本正经:“我想抱着你充电,以后可以不锁门吗?”
他苦笑道:“翻墙挺累的。”
粟软之后探头出去才知道沈妄口中轻描淡写的“书房与主卧阳台连接着”是什么意思。
书房和主卧的确都有阳台,但中间隔着快一米的间隙,且没有任何扶手。
此刻,她只是一脸头疼:“你又在套路我。”
昨晚在床上。
他嘴里就没一句实话。
嘴上哄着她说的出什么都好听。
实际上,一下比一下致命。
粟软今天腰都还酸的。
一个人,怎么能长着一张斯文禁欲的脸,看起来正人君子,背地里却如同饿狼捕食,且习性变态的?
昨晚那些姿势。
粟软都不知道,沈妄是用哪个脑子想出来的。
沈妄没说话,只是搂着她的腰待了好一会儿,才让她去洗澡。
早餐吃到一半,赵轩从外面走了进来。
沈妄看了眼手表,桌上的饭也没吃完,就放下了筷子。
粟软看了眼赵轩,又看向沈妄:“你不吃了?”
沈妄颔首:“我要去镜城一趟。”
说话时,他递给粟软一张卡:“你在家乖乖等我。”
“最快两天就可以回来。”
他一边说着,接过佣人递过来的帕子擦拭着手,垂眸挡住眼底的不舍:“若是有人欺负你。”
“等我回来给你撑腰。”
想到什么,沈妄抬眸,格外深邃的眸子盯着粟软,轻笑道:“当然,在北城,你也可以打着我的名号做任何想做的事。”
“就是捅破了天,我也能给你补上。”
这是沈妄对粟软的独家纵容。
就像当年,他也是这么娇惯着她。
小时候的粟软尚且收敛着,始终觉得自己寄人篱下,要懂事、要听话,被人欺负了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怕添麻烦。
但,此时此刻,24岁的粟软把沈妄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
她也清楚的知道,无论她做什么,沈妄都会给她兜底。
当即,粟软明媚一笑:“好啊。”
“我要把天给捅了,你可别生气。”
沈妄挑眉,沉冽的眸子下,是少见的狂妄:“捅破了天,算我的小天鹅有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