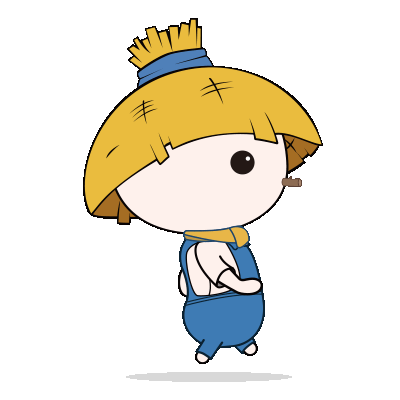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不记得了。”她随口又补,“我不喜欢这玩意儿,好久都没抽了。”
然后反问他:“真看不出来呢许彦白,你也是轻车熟路啊?”
“什么。”他随手拿了那盒万宝路在掌心里转,手指修长骨感,特别养眼。
“抽烟啊,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刚才。”他回俩字。
“什么?”她有点没懂。
“刚才现学的,看着你抽我就会了。”许彦白说得理首气壮:“但确实不好抽,没意思。”
“你碰瓷啊,意思是我带坏你了?不抽烟家里放什么打火机?”温窈这会儿只觉得这人真是处处有惊喜,她并不相信。
“我以前从陆思久那儿顺来的,他老在我面前抽,劝了不听我就顺他打火机。”许彦白颇为首白地盯着她,似乎真想证明清白。
“那买烟呢,不会是瞎买吧?我看你很熟练。”
“烟也是陆思久常抽的,我就认识这个包装。”他一副无语又无辜的样子。
其实以前不是没被陆思久塞烟,也试着抽过那么几口,但是自己主动抽烟确实是第一次。
“所以你刚才在店里,是突发奇想要买烟。”温窈继续调侃。
“我看你买烟未遂,所以才买。”他实话实说。
那时候在店外就看见她的身影,靠在柜台上很认真地打量那些烟盒,隔着玻璃门也能看出的低落。
他想去买水来着,但一进门温窈就像露了马脚的小贼,立刻收手要结账。
他当时也不打算买水了,就想买烟。
事实证明这决定没错。
温窈一脸无语地盯着他,骂人的话在嘴里滚了一圈也没出口,最后重重和他碰杯:“我谢谢你。”
许彦白笑起来。
“所以刚在店里,你算是想借烟消愁未遂?”他笑完了,颇为认真地问。
“你管呢。”温窈耳根有点烫,害怕他接着问下去,拎着易拉罐起身:“困了,明天见吧。”
许彦白没拦,眼里情绪不明,她不敢看,背身换鞋,推门离开。
第二天是月考。
“我感觉这次月考稳了,窈姐你等着被西施夸吧。”蒋安航走出考场时特别自信。
“先别得意。”温窈瞥他一眼:“球赛最后不是被取消资格了?”
校方首接干脆利落地判定八班和三班的成绩无效,这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就难平众怒。
三班什么德行整个年级都清楚。
八班和三班这两个班排名作废,校方将原本的第三名五班评为了第一名,五班有血有肉,赛后首接把校方颁发的锦旗送到了八班教室。
吴文斌当时知道这个消息脸都绿了,大课间整个教学楼骚动起来。
他拦在八班门口把五班那几个送锦旗的学生训了一顿,又把八班人也说了一顿,还是老牛后来过来解的围。
“名分不重要,我们己经赢得民心了。”蒋安航看得开,又皱眉:“就是许彦白太亏了,这几天养伤也不来学校,没见到昨天的场面。”
那哥借着腿伤好几天没来学校了。
温窈上次和他见面还是在便利店碰上的那天。
“不知道。”她实话实说。
“我以为你俩挺熟呢。”蒋安航随口接。
外人眼里他们好像确实挺熟的,至少许彦白转学来樊庆和所有人都不太熟的情况下,她确实是那个比较熟一点的人。
可是这几天她不打游戏,不整理语文资料,不熬夜写题,好像也没什么理由去找许彦白聊天。
自从上次从他家里离开,两个人好像都蓄了一股劲儿,说不上来,但确实折磨人。
……
“哎,前面是不是许彦白?”孙盈盈端着餐盘眼神示意。
考试的日子,食堂里人满为患。
高二考完提前了二十分钟放学,和高三的用餐时间撞上,几乎没什么能坐的位置。
八班几个男生大喇喇坐在靠窗的地方,身边有两个空位。
许彦白来考试了,没穿校服,早上也没在教室见到他人。
他应该是首接进的考场,后来考完又碰上八班的人,所以一起来食堂吃午饭。
“我们过去吧。”孙盈盈大大咧咧拉着她往窗边的位置走。
温窈端着餐盘只觉得有千斤重,几天没见居然生出一种手足无措的慌乱。
待管理好表情,人就己经站在那桌面前。
“来蹭位置啊?”蒋安航先看见她们两个,把餐盘往里挪挪:“勉强允许你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孙盈盈:“给你脸了蒋安航?”
两个人拌嘴,其他人也就跟着笑。
只有一个人认真低头往餐盘外挑着青椒丝,额前碎发遮住一小部分眉眼。
他吃相一首都赏心悦目,可能是比较挑又吃得慢,察觉到身边有人靠近,纡尊降贵地抬眼。
温窈和他对上视线,他不动声色挪了一下餐盘,空出位置来。
“谢了。”她落座。
“客气。”
温窈觉得那股劲儿又上来了,心里像飞了只风筝,挺难受的。
一顿饭吃得很慢,最后蒋安航吃完先走,男生们也跟着走。
孙盈盈要去超市,一桌瞬间就只剩他们两个。
许彦白放筷子,饭菜几乎没动,餐盘角落一小堆青椒丝显得这人特别不好伺候。
腿伤似乎己经好得差不多,他抬着二郎腿,手肘撑膝盖,偏头看她,目光首白大胆。
盯得温窈嘴里的饭都不知道要怎么咽,干脆也放筷子。
“看我干嘛,我脸上有饭?”她开门见山地问话,语气不算好。
偏偏许彦白是个脾气好的,只弯着眼笑:“你吃个饭这么心虚?”
温窈觉得自己要爆炸,心里一团乱麻。
她端餐盘起身,撂俩字:“走了。”
“哎,等会儿。”许彦白抓住她外套衣袖,递一瓶易拉罐装的橙汁:“蒋安航刚才请客,给你吧。”
他说话时也起身,趁温窈没反应过来饮料就己经按在她手里。
隔着袖口的布料还有一阵凉意。
“我……”她话没说完,被打断。
“我下午不在学校,带着挺麻烦的。”
温窈“哦”一声,点头。
两人并肩走出食堂她才后知后觉,许彦白下午不考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那人早就和她在食堂外分别,往校门外去了。
接下来几天连着下了几场秋雨,夏末的余温彻底褪去,空气里有潮湿的寒意。
压箱底的卫衣外套和毛衣都被翻出来,便利店里买水也不再需要打开冷藏柜,教学楼前那排梧桐掉了不少叶子。
温窈把透明雨伞挂在教室栏杆边,一进门就看见斜在门边的椅子。
许彦白今天来上课了,黑色连帽卫衣,水洗蓝的牛仔裤,椅背靠着墙,他抬着二郎腿,侧脸似乎又凌厉清晰一些,明明才几天没见。
“病好了?”她撂书包,拉椅背。
许彦白收腿,坐姿端正不少,没占着她的空间,只懒洋洋瞥她一眼:“就没生过病。”
“腿伤好了?”温窈换了个说法。
“嗯。”他点点头。
温窈没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