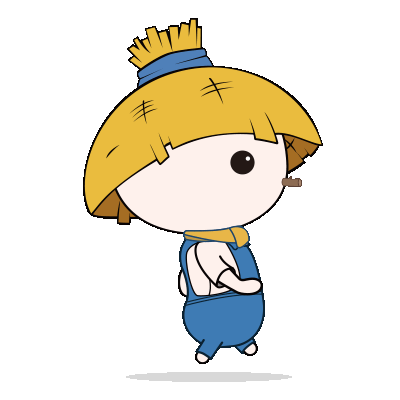那时候,云予薄稍微带有冷意的眼神,就能让她直接跪在地上,紧张的复盘自已又做错了何事。
她有认真的学,有好好的完成功课,也有去听云予薄的教导,将其记在心中。
继位后,她褪去那些刮得皮肤生疼的粗衣,换上了柔软真丝锦袍,整个人都如脱胎换骨。
“好漂亮……”
选衣时,祁昭浅的手不自觉摸上那些布料,心中竟也生出了一丝欣喜,一份得意。
这些,是她以前的奢望,她从未敢想,如今要穿在身上,只觉是在做梦。
看着上面精细的做工,富贵的图案,祁昭浅有些恍惚,想到了什么。
她记得母妃有一件舞衣,料子也是极好的,冰冰凉凉,穿在母妃身上柔软飘逸,让人移不开眼。
母妃总将那舞衣抱在怀中,深情痴恋,爱不释手。
看着她那样子,祁昭浅总觉得这算是……睹物思人,回忆往昔。
至于她为什么知晓料子好,是因为她偷摸过。
某日,她看着那流光溢彩的舞衣,终是按耐不住心底的好奇,在母妃睡着后小心翼翼的伸手摸了摸。
她手上的茧很厚,只只柔软和冰凉,其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她不明白,眼里都是疑惑,
下一秒,祁昭浅的手腕赫然被抓住,对上了母妃凌厉的双眸,让她心尖一颤。
她以为自已已经足够小心,但还是被自已母妃抓了个正着。
祁昭浅的脑子空白一片,哆嗦着开口。
“对……对不起,母妃。”
她话语刚落,母妃便抓着她的头发,将她甩了出去,怒不可遏。
母妃的力气极大,祁昭浅被砸到墙上后又落到地上,扬起了一地的灰尘。
粗粝的石子划破她的衣衫,肌肤瞬间鲜血淋漓,火辣辣的疼。
她咬唇仰头,母妃正细细看着那衣衫,检查是否有破损,是否有污渍。
许久后,母妃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转身对着她便破口大骂起来。
“你也配碰?你可知这是什么?贱蹄子!这是阿渊给我的!”
听见这些话,祁昭浅低下了头,不言语一句。
她愣愣的听着自家母妃骂她下贱,骂她恶心。
习惯了,可还是闷得厉害,心也疼得厉害,像是被人紧紧地攥住,无法呼吸。
“你这样的人!什么都不配!只配下地狱!不得好死!”
母妃又开始发疯,不知把她当做谁,疯狂的咒骂着,宣泄自已的不满,甚至又给了她两个巴掌。
巴掌打在脸上,祁昭浅眼眶通红却落不下泪。
她在那一刻觉得,凡世间之美好,都同她无关,但凡稍微好一些的东西,她都不配,她只适合做污泥,众人厌弃。
母妃不发疯时,又好像很好,会给她讲当年的京城趣事,描述繁华的酒楼,喧嚣的街道,才子佳人的浪漫,让她心中生满向往。
所以,她才渴求自由,想要去亲眼去看看,于群山之巅,看大河奔涌,于群峰之上,感受长风浩荡,而不是在宫墙里,卑躬屈膝,苟延残喘。
祁昭浅垂眸,压住心底的悸动,不打算再想。
那件舞衣,在母妃死后,便被她扔进了火堆,化作了灰烬。
她一直认为,这衣服是自已那父亲皇祁渊给母妃的赏赐之物,是让母妃疯魔的罪魁祸首。
她未曾见过自已的父皇,只在别人口中零星听到过几句,但评价,基本都算不得好,贬低之词颇多。
不过无所谓,他的位置,最终轮到了她这个弃子身上。
祁昭浅微微勾唇,拿起那些衣裙,将它们穿到了自已的身上。
在此期间,她还想到了大公主祁昭宁。
那个风光无限,最后却落得身首异处的长姐……当真是造化弄人。
而她也明白,有些东西需得靠争抢才能得来,而心狠者,绝爱者,方可夺天下。
换好衣裙后,祁昭浅便去了书房。
云予薄很早便在书房里,手上拿着戒尺,面上冷漠,看见她后,只微微点头。
祁昭浅给她行礼,坐到了书案后,垂眼看着今日的课程。
日子多枯燥乏味,祁昭浅以前未曾接触到过这些东西,让她觉得很是无趣。
她觉得学习是一种煎熬,加上云予薄的严厉督促,她虽用功,但进展缓慢,每日都在焦躁的边缘。
云予薄在教导她一事上,并不嫌弃她,显得很有耐心。
刚开始习字时,祁昭浅惧怕云予薄,握笔的手止不住的发抖。
后面相处的时间多了,她才压下心底的恐惧,可以握笔,可以书写。
“帝师,这样可以吗?”
寻常一日,祁昭浅小心翼翼的问着云予薄,脸上都是紧张。
听见这话后,云予薄放下自已手中的事,看向了她面前的纸张。
上面字迹歪歪扭扭,一些大,一些小,很多连笔画都不对,看着着实……碍眼,让人不忍直视。
她单看了一眼,微微皱眉。
云予薄这神情吓得祁昭浅的那沾满墨水的笔落在了纸上,晕开一大片。
“我……我再写,太傅别生气。”
祁昭浅赶忙把那废纸拿起放在一旁,换上了新的纸张。
可她好像太笨了,看见那些书籍心中就没来由的害怕和烦闷,因为课业,她每晚都得很晚才能睡觉。
强压之下,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昏昏沉沉。
云予薄哑然,看她自觉,便不好再说些什么。
对比起她才教祁昭浅时,已经好上很多,至少能看出来写的什么字。
她这几日很忙,没心情再骂她,祁昭浅还算努力,那今日便不挑她的错,让她自已学着。
云予薄把目光撤下,看向了眼前的书。
房中静谧,只有书籍翻动和落笔写字的声音。
许久后,祁昭浅有丝倦怠,垂眼看着自已的狗爬字。
还是有些丑,她不敢拿给云予薄看,看了后,必然又是让重写。
祁昭浅余光看向了云予薄,想着怎么开口。
不知何时,云予薄已经放下的手中的书,杵着头在桌边浅寐,宁静外表遮掩了素日的严厉,好看的眉目间也没有忧愁,不再皱起。
祁昭浅愣神,决心不打扰她,也算是自已偷偷懒,松懈片刻。
恰巧,窗外有飞鸟飞过,祁昭浅分了分神,侧头看着它们。
它们在空中嬉笑玩闹,叽叽喳喳,似有无限乐趣,畅谈天地间美好。
“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