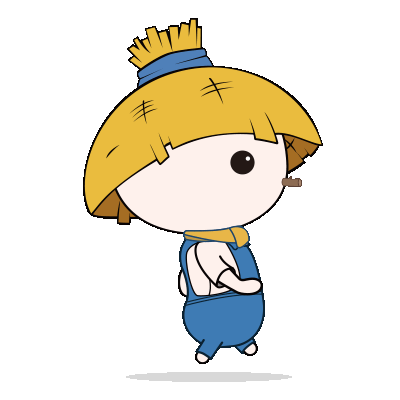这些大臣,说的都是实话和事实,她也确实如此,除了心狠手辣,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有,别人不服气她,倒也正常,她都找不到自已能让人臣服的点。
祁昭浅看得很开,在冷宫时,早就有了不去听耳旁风,把所有话语都置之度外的技能。
若是什么话都听进去,那她可活不到如今,恐怕早就郁闷死了。
看着那些大臣因为她无所谓的态度而气得吹胡子瞪眼,她心情多少有些美妙,甚至享受这种别人看不惯她又干不掉她的表情,别提多惬意。
她早就知道自已登位后必然会迎来批斗大会,不过无所谓,云予薄会替她摆平一切,她只需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当个花瓶就好,别的都无需她出手。
党派之间争执严重,骂得唾沫横飞,甚至有要打起来的趋势。
祁昭浅坐在位置上看戏,将骂她的那些大臣都记在了脑子里,决心以后要是有机会,一定好好收拾。
最终,还是云予薄出面平息这场闹剧,让祁昭浅的地位更巩固了一分。
“够了!”
正是吵闹的时候,两方吵的不可开交,大殿门毫无征兆的被人打开。
云予薄逆着光站在门口,周身都是凌冽气息,不少人心底一惊。
她这句话威慑力十足,让整个大殿陷入一片寂静,全部回头看着她。
云予薄站在光里,如白雪一般皎白无瑕,让人不敢靠近,不敢直视。
随后,除顾琅和几位不服气的大臣外,别的都讪讪分到两边,自觉的排好站好,仿佛刚刚大吵大闹的不是他们。
之前他们得的消息,说云予薄出宫了,暂时不会回来,这才敢来批斗祁昭浅。
怎么现在,回来得毫无征兆不说,还让人内心十分惶恐。
祁昭浅抬头看着云予薄,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忙唤她。
“太傅,你可算回来了,他们吵的太久了,还是太傅来定夺吧。……”
她话语说得可怜,云予薄眯了眯眼,环视着四周。
她看着那些大臣,摆了摆手。
随后,她身后涌进大批士兵,将大殿的里的人团团围住,手中的剑对准了他们。
“云予薄,你这是作甚?这里是朝堂!容不得你放肆!还不把你这些兵撤下去!你一个文职,哪来的兵权!”
顾琅站出来质问于她,云予薄连正眼都没有给他一个。
她不慌不忙的走向前,踏上了台阶,走到了祁昭浅的身前。
祁昭浅看着她走上前,坐在位置上的她欲起身,但云予薄眼疾手快按住了她的肩膀,示意她不必动。
她有些懵,侧身躲了一下她的手,但是没躲过。
祁昭浅惧怕她,所以会不由自主的想跑,身体会无端想要反抗。
云予薄自然是感受到了,这无疑触碰到了她的逆鳞。
她按祁昭浅肩膀的手微微用力,祁昭浅有些疼,咬唇不说话。
祁昭浅知道,云予薄是在给自已下马威,也是在给这群人下马威。
她想让谁成为女帝,谁才是女帝……这一点毋庸置疑。
云予薄转身,目光森冷,扫视站在下面的每一个人。
她冷笑一声,平静开口。
“作甚?我还想问太尉你要做甚?公然在朝堂质疑陛下,拉帮结派,口出不逊!我为保护陛下而来,怕她被歹人刁难,我受先帝之令辅佐陛下,这兵权自也是先帝授的,你们究竟有何异议?到底是谁更为放肆?今日便在此说清楚!”
她的言语中透露出威严,面上却没有丝毫情绪波动,这是身居高位者的独特表现,让人心生畏惧。
“你!纵使先帝遗诏在,可拥护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稚子有何用?”
顾琅气急,周围也有人小声附和着。
“太尉言之有理,太傅何必如此古板?剩下的几位皇子公主里,随便拎出来一位,恐也比十一公主好。”
“国本不稳,北陵建朝不过十余年!民心未归,怎能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接手。”
“……”
这些话语都落进了祁昭浅的耳朵里,让她忍不住八卦了一下
她听人说起过,当年百姓不满前朝奢靡浪费和高额赋税,遂揭竿而起,跟随端王造反。
她父皇便是起义中的一员,对端王忠心耿耿,后面逐渐得了人心,势力壮大,成了小头目。
前朝被架空所以不堪一击,端王势力和前朝势力对抗,隧两败俱伤,谁也没有捞到好处。
祁渊这时候带人冲进了皇宫,杀了前朝皇帝,可端王也因为伤害过重一命呜呼,至此,祁渊被众人拥护着坐上了皇位,直接称帝。
祁渊开仓放粮,救百姓于水火,被百姓所称颂。
但他本就是粗鄙之人,打架他在行,治理国家一事上,还得他人辅佐,不然他的脑子,真想不了过多。
当年他跟随端王时不必担心这些事情,只负责听令行事,如今他周围都是一群当年跟随他起义的……这就让他很是头疼。
勉强撑了几年后,消磨掉了他所有的耐心。
祁渊从未觉得有任何事比管制一个国更让人窝火和烦闷,开仓放粮时他大方,可有别的灾情时,便什么都拿不出来,安抚不了各地百姓,甚至又要激起民怨。
祁渊焦头烂额之际,云予薄出现了。
彼时的她正年少恣意,人尚青涩,人人都觉得她不行。
可她聪慧过人又有勇有谋,还会观星卜卦,被祁渊另眼相看,夸赞连连。
她给祁渊觐见众多方法,教授祁渊如何管制,祁渊总说云予薄是上天给此国派来的孔明,云予薄通过自已的努力,成功谋得少傅一职,也得了不少百姓称赞。
在云予薄的帮助下,动荡渐稳,百姓终于不再怨声载道,边疆也安稳下来。
能者为王是永恒之理,但在奢靡的的熏染下,祁渊竟也忘了本心,开始逐渐走向那欲望的枷锁。
云予薄忠心于他,坐着虚职却谋着实事,祁渊放下心中戒备,对她的能力越发赞赏,可这些,终成了刺向自已的利刃,他把一把刀,带在了身边七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