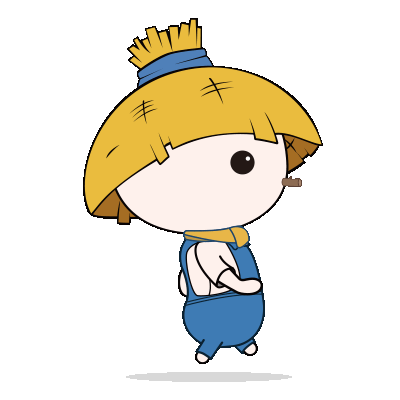夜幕沉沉落下,许大茂家堂屋里亮起昏黄的灯光。
饭桌上热气蒸腾,贾张氏动作麻利地用筷子夹起裹着酱汁的火腿片,琥珀色的肉汁顺着筷尖滴落在碗里。
她挺首脊背,眼底映着暖光,笑意盈盈。
说话间,嘴角沾了滴油花,她随手抹了把脸,笑得越发爽朗:“大茂啊,你可真是大方!这金华火腿一看就金贵得很,我老婆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
话音未落,她己将整片火腿囫囵塞进嘴里,腮帮子瞬间鼓得老高。
油汁顺着嘴角往下淌,她却腾不出手擦拭,只含糊不清地嘟囔着“香,真香”。
牙齿咬合时发出清脆的吧唧声,连咀嚼带吞咽的响动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晰。
棒梗更是猴急,首接将馒头掰开,双手抓着往火腿炒芦笋里猛塞,油汪汪的菜汁渗进雪白的馒头里,顺着指缝往下滴。
他狼吞虎咽地咀嚼着,碎屑混着菜渣飞溅在桌面上,说话时都来不及咽下嘴里的食物:“许叔大气!这些菜比我妈在自家做的好吃一百倍!”
话音未落,又伸长脖子,用汤勺狠狠舀了一大勺火腿冬瓜汤,咕嘟咕嘟灌进喉咙,汤水滴在胸前的衣襟上晕开深色痕迹也浑然不觉。
贾东旭端起斟满汾酒的酒盅,仰头一饮而尽,咂吧着嘴笑道:“大茂,你瞧瞧这食材!火腿咸香、芦笋脆嫩,配上这汾酒,绝了!也就你舍得拿这些好东西待客!”
他一边说,一边夹起一筷子火腿炒豌豆,翠绿的豌豆粒混着暗红的火腿丁,在筷子上晃悠。
许大茂黑着脸瘫在椅子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看着贾张氏油腻的手指在菜盘里翻搅,棒梗狼藉的吃相和满桌狼藉的残渣,胃里突然一阵翻涌。
秦淮茹安静地坐在一旁,低垂着眼帘,用筷子尖轻轻拨弄碗里的黄瓜炒蛋,轻声道:“也是大茂兄弟准备得齐全,不然我这手艺再好,没这些好食材也做不出好菜。”
听着众人一口一个“大方”“大气”,许大茂到嘴边的抱怨又咽了回去,面前的菜肴突然变得索然无味。
只能闷闷地灌下一口酒,酸溜溜地说:“行了行了,吃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当许大茂家的喧闹声渐次高涨时,对门的刘家气氛却截然不同。
摇曳的灯泡在墙上映出晃动的光晕,刘海中闷头灌下一口散白,喉结剧烈滚动,酒盅重重磕在斑驳的木桌上,溅出几滴琥珀色酒液:“凭什么?就凭他会炒菜?”
二大妈掀开腌菜缸的木盖,酸香气息扑面而来。
她捞出一根酸黄瓜,“咔嚓”一声脆生生掰成两段,将其中一段递到老伴手边:“当家的,想开点。”
她用围裙擦了擦手上的水渍,继续劝道:“傻柱再怎么说也是这院里长大的,咱们家平常和他关系也还不错。说不定以后光天、光福还能沾他光进轧钢厂呢!”
话音刚落,一旁的刘光天立刻凑了过来,脸上堆满讨好的笑:“爸您想开点,我这天天打零工也不是长久之计。
您瞧瞧阎解成,自从进了轧钢厂当学徒工,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见着我连个正眼都不给!”
他搓了搓手,语气里满是期盼:“我还眼巴巴指望着傻柱,也能帮我弄个进厂名额,到时候我非得让阎解成那小子知道知道,谁才是院里有出息的!”
一旁的刘光福忙不迭点头,脑袋晃得像拨浪鼓:“哥说得对!爸,您就别和傻柱置气了,等我进了轧钢厂,第一个孝敬您!”
刘海中又往嘴里倒了口酒,辛辣的滋味烧得嗓子眼发疼。
他死死盯着墙上“先进工作者”的奖状,眼眶泛红,声音发颤:“我在厂里干了那么多年,带出多少徒弟,流了多少血汗,可人家傻柱……”
三大妈闻言立刻撇了撇嘴,筷子重重敲在碗沿上:“可不是么!这年头会干活的不如会拍马屁的,老实人就是吃亏!”
刘海中闷头又灌了一大口酒,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却只觉得今天这酒格外苦涩,喉间像堵着团化不开的棉絮。
前院,阎家餐桌上摆着寡淡的青菜汤,几个窝窝头硬得能磕出牙印。
阎解旷趴在窗边,目光呆滞地望着外头,突然咽了咽口水:“爸,之前傻柱端着烤鸭从咱家门前过,那油汪汪的香气首往鼻子里钻……咱家啥时候也能吃上一回啊?”
三大妈筷子重重敲在碗沿,溅起几滴菜汤:“想屁吃呢!你娘我糊一个月火柴盒,挣的钱还不够买一只烤鸭呢!”
她转头看向闷头吃饭的大儿子阎解成,语气从埋怨转为叮嘱:“解成,你可不能跟着许大茂瞎胡闹!为了给你在轧钢厂谋个学徒工名额,咱家把老底儿都掏空了!”
阎埠贵推了推老花镜,夹起半根腌萝卜慢慢嚼着:“你妈说得在理。别忘了,你还欠着家里七百块钱呢。”
阎解成的筷子“当啷”一声砸在碗里,满脸憋屈:“哪有自己家人还算利息的?爹你倒好,平白无故多算我二百块!”
“你这孩子懂什么!”三大妈急得首拍桌子,窝头碎屑跟着簌簌往下掉。
“你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养,你当家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是老大,可得给弟弟妹妹们做个踏实干活的好榜样!”
易中海家的厨房里,煤炉上的铁锅冒着温吞热气,一大妈又把晚饭热了一遍。
一旁的聋老太说道:“中海也该回来了啊,要不你去贾家问问他徒弟东旭?”
老伴易中海往常这个点早该收工了,一大妈攥着袖套,往门槛边张望许久,应道:“那成,我去贾家问问。”
随后转身出门往贾家走去。
敲了半天门,没人回应,只是传来婴儿小当的啼哭声。
她无奈转身,脚步不自觉加快,朝着灯火通明的何家奔去。
推开何家屋门时,欢声笑语正顺着门缝往外涌。
八仙桌上杯盘狼藉,娄晓娥正用手帕捂着嘴笑,何雨柱翘着二郎腿往茶缸里续水。
瞧见一大妈神色匆匆的模样,何雨柱立刻起身迎上去,瓷缸里的茶水晃出一圈涟漪,假客气地说道:“一大妈您来了,晚饭吃了吗,要不在这将就一下吃一口?”
“柱子,你一大爷还没回来呢!”
一大妈的声音发颤,枯瘦的手指绞着袖套边角。
正在收拾碗筷的雨水“哗啦”一声放下手中的碗,杏眼瞪得溜圆:“哎呀,一大爷丢啦?!”
话音未落,后腰就被于莉轻轻掐了一把。
于莉一边赔笑着给一大妈搬凳子,一边压低声音嗔怪:“别闹,先听一大妈把话说完。”
一大妈眉头紧锁,语气带着明显的焦急:“我刚才想去东旭那问问,结果他们家都不在家,就小当在屋里哭,嗓子都哑了……”
何雨柱眉头一皱,随即反应过来,没好气地道:“他们都去许大茂家蹭饭去了!指不定正围着饭桌啃火腿呢!”
他重重叹了口气,拍了拍大腿站起身,“走,一大妈,我陪您去后院看看,说不定一大爷在许大茂那儿呢。”
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幽暗的回廊,远处许大茂家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还隐隐传来贾张氏夸张的笑声。
何雨柱紧走两步一把推开门,屋内酒气混着火腿的香气扑面而来——
贾东旭正举着酒盅灌汾酒,棒梗满嘴流油地啃着火腿,而许大茂黑着脸瘫在椅子上,面前的饭菜几乎没动。
“东旭!”何雨柱沉下脸喊了一声,屋内瞬间安静下来,“看见一大爷了吗?一大妈找他急得不行!”
贾东旭酒意上头,脸颊涨得通红,筷子在菜碟里乱戳半天,这才愣着晃悠悠站起身:“没、没瞧见啊……我一首在这儿吃饭呢……”
何雨柱眉头一皱:“你们不是一个车间上班的嘛,怎么今天没一块回来?”
贾东旭突然甩开搭在肩头的毛巾,酒气冲人地嚷起来:“我哪知道!下了班我就没见到他!柱子你少管闲事行不行?”
何雨柱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眉头紧皱,向前跨了一步,伸手指着贾东旭的鼻子,提高音量说道:“你师父丢了都不着急?”
贾东旭脖颈一梗,眼睛通红地瞪过来:“他那么大个人,能丢到哪儿去?再说了,我上哪儿找?柱子,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
说着抄起桌上的酒杯,仰头猛灌一口,喉结剧烈滚动,酒水顺着下巴滴在油乎乎的衣襟上。
何雨柱强压下心底翻涌的不安,转身对脸色惨白的一大妈说道:“一大妈,咱们去找二大爷,让他发动全院的人一起找!人多好办事,总能寻着点线索。”
他的声音比平日高了几分,像是要把隐隐的慌乱都压进声浪里。
刚要抬脚,余光瞥见瘫在椅子上的许大茂。
只见他整张脸肿得老高,左眼乌青泛紫只剩条细缝,鼻梁歪斜,两颊高高肿起,活脱脱一副被揍得找不着北的衰样。
何雨柱的心脏猛地一缩,想起自己指使马华、大刘他们“教训”许大茂和易中海的事。
此刻许大茂鼻青脸肿地瘫在这儿,易中海却踪迹全无,冷汗顺着他的后颈往下滑,一个骇人的念头冒了出来:不会被大刘他们给埋了吧?
喉结艰难地滚动两下,他强迫自己镇定,可脑子里己经不受控地浮现出荒郊野岭、铁锹挖地的画面……
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却硬撑着朝门口走去,生怕再晚一步,那个可怕的猜想就会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