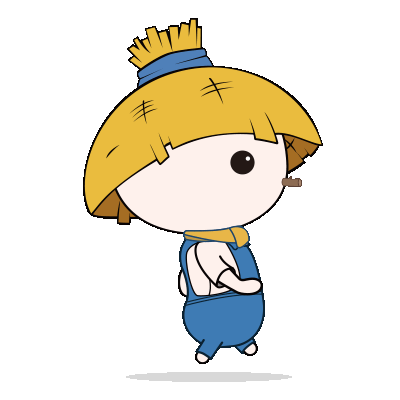无声的悲鸣响起,过于强烈的痛苦甚至化作实质,令空气为之颤栗。
玫久的脑袋变换出种种形状,像极了一团不稳定的物质。
她不再慢慢爬行,而是发疯一般冲向自己的身体,却又在身体前停了下来。
方才还在阿莱雅身旁的那把剑,如今已经贯穿了她那蜘蛛躯壳,将她的身体牢牢地钉在地面上。玫久愣了片刻,脚步声在她的身后响起——
“还在找什么后路吗?抱歉,这世上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所了。”
玫久的脑袋没有动,但红色的眼睛一瞬间就转到了脑袋后面。
利德与阿莱雅站在一起。
风很大,吹起两人被打湿的衣摆。
利德仅有的那只手高高举起,虚握着一股奔涌不歇的力量。只一眼玫久就认出来了,那是利德独有的力量:他是人类当中唯一一位在所有武道上都臻于圆满的人,所以他不需要武器就可以自由的驾驭剑气、刀风、枪势、拳罡……他即是百兵之主,再强的武道也需向他俯首。
而他也可以将此种种气机外放,汇聚到一起,使一拳一脚间亦有百兵之威能,变幻莫测。这些在交战的时候玫久已经亲身体会过了,如果不是仗着无与伦比的强横躯体,她也抗不过这种人间武道的极致展现。
只是这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劳累,利德手中的力量似乎也有些难以驯服,它不断地变换着形状,有时像刀、有时像叉、有时像斧……
黑泥般的首级中传来玫久阴冷的笑声:
“看来你也有不受命运眷顾的时候,永远地失去了最顺手的剑气,其余武道再也不能如臂指使——”
她的笑声戛然而止。
因为,就在利德的身侧,阿莱雅握住了利德举起来的那只手。
汹涌的剑气从她身上汇入利德的手中,那团变幻莫测的力量缓缓凝结成了一把直指苍穹的银白长剑,光芒刺得她不得不移开视线。
狂风在两人的周围汇聚,风暴中心的主仆纹丝不动。
“并非是【失去了剑气】,而是【不再需要剑气】了。”
她听见利德平静的声音。
那声音犹如教堂内回响的晚钟。
“再见了,寄生在神皮里的渺小灵魂啊。体验卡到期,梦也该醒了。”
银白色的剑刺穿天际,乌云纷纷退却。长剑带着耀眼夺目的光落下,利德最后一句话也永远地留在了玫久的脑海。
“不必心急,终有一日,我也会把那些你顶礼膜拜的上三族一同送葬。”
黑泥般的头颅被切成两半,没有任何血流出,但一股力量却猛地汇入天地之间。
就仿佛无数悲哀的灵魂终于得到了解脱,清新的风吹过腐朽的土地。
……
玫久的视线定格在并肩站立的阿莱雅与利德,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秒,一段画面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那是她年轻的时候,也曾像这样与谁并肩过,那人同样生得丰神俊朗,但他们二人的神情却与利德、阿莱雅完全相反:年轻时的玫久巧笑嫣然,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却神色淡然。
——西秦领主应同。
南楚领主向慕曾说他外表坚韧,却缺乏足够的胆魄,因此总是寄希望于外力。玫久倒不这么看,她觉得应同与向慕就像一根线的两端:向慕生来洒脱,年少成名,睥睨世间万物,活得潇洒恣意;而应同上位领主的过程并不顺利,所以他性格谨慎,心中却有一团扑不灭的火,想做一番大事业,让自己的名字悬日月而无穷、炳天壤而不朽。
玫久觉得自己的性格更像应同,所以她对向慕的好感要稍微多一点。人们通常不喜欢太像自己的人,总觉得对方能够轻易看穿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但她还是与应同并肩的时间更久,西秦需要深渊教会,深渊教会也需要西秦。一位美女被两个领主惦记,固然是因为她足够出色,但这背后也必然会有种种利益牵扯。历史总是喜欢把这背后的利益拿掉不讲,转而渲染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戏码。
深渊教会帮西秦将民众变为不知疲倦的怪物,迅速让这个领地强盛起来,但反过来这一切也是在为玫久飞升成神做准备;
应同知晓并利用了玫久的计划,想要借无数人的怨魂煞气重塑先贤荣光,让人类在自己的带领下回到硬抗上三族的全盛时期;
玫久同样将应同的打算尽收眼底……
在这种“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可笑循环中,两个人的底牌互相展示,互相容忍对方的肆意妄为,互相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他们都相信赢家会是自己,所以在无数个日夜中,他们并不居住在一起,却坐在同一张赌桌前。
其实这个赌局一开始是不成立的,因为煞气无法脱离实体长期聚拢在一起,而能够充当“媒介”的天厌之子从未活过十八岁,应同手里一度是必输的死局。
然而恰恰就是因为利德在朝北行中救下煌颜,这场赌局居然又神奇地被拉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两个人都准备了太久,没有收手的可能性了。
天生万物总有残缺,每个人也不例外。玫久与应同是一类人,心中的执念催促着他们向更高的地方攀登,哪怕一步踏错就是万丈深渊。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玫久如愿成为了神明,飞升的美妙感觉让她陶醉其中;四面八方的煞气也像见到肥肉的狼一样扑向煌颜,先贤似乎很快就可以降临在这片土地,重新带领人类走出危困。
但命运充满残酷,它从不在乎你做出了怎样的谋划。人间各种荡气回肠的故事,最终仍然要以胜败二字收尾。
玫久突然想起来,不久之前也是一个雨天,她坐在庭院里小憩,风尘仆仆的女儿诗鸢赶回来,向她报告南楚领主与贵族之间的恩怨落下帷幕。那天玫久让诗鸢不要再见利德,那天,诗鸢问了玫久一个问题。
——“妈,我能问你个问题……你喜欢过南楚领主吗?”
——“大概吧。”
——“那你喜欢过西秦领主吗?”
——“嗯……或许吧。”
诗鸢听完气鼓鼓地离开,很明显对母亲的答案不满。
玫久笑而不语,她的回答永远都是这么随性,但这其实也是她的真心话。当时她发自内心地觉得,无论这段感情是否存在都无所谓,而且她知道西秦领主应同也是同样的想法,不然他不会在某次欢好后说出那句“我们的未来中没有爱情的容身之所”。
他的内心或许还有些微愧疚,所以他才会作此感慨。玫久就不会,她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这些事她从来都无所谓。
直到死去的那一刻,跌落神坛、重入人间的她才产生了些许疑惑。
若是有情,在两人同床共枕的年月,为何她不愿放下心中成神的执念与他长相厮守?
若是无情,她又为何会在生命的最后,想起诗鸢问过的这个问题呢?
……
巧合的是,就在玫久身死魂消的那一刻,影先生也栽倒在小白的怀里。
他的眼神中有释然,或许觉得死在小白手上对自己是一件好事;但也有不甘,因为他清晰地感知到先贤并没有重新降临——那无边无际的煞气没能吞噬天厌之子,相反,天厌之子吃掉了它们。
竹篮打水的又岂止是玫久?
在这场浩劫中,她的目标没有成功,应同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小白收了剑,很有风度地扶着这位败在自己手下的中年男子,低声说道:
“雨停了。”
影先生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笑了笑,回答:
“是啊,一切都结束了。”
当惨淡的阳光投射到这片已成废墟的土地上时,小白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埋藏在他心里许多年:
“对这一切,我并无半点开心。无论如何,你们都是我的父母。你对她有感情吗?”
影先生抬起头,望着看不到的远方,语气低沉而快速:
“你的父亲死在向慕的手里,我不过是借尸还魂的怪物,一团继承了他记忆的【影子】罢了……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或许你的父亲也不能。等他们到了地狱,再当面盘算这些小事吧。”
……
当一个人朝心中的圣地狂奔的时候,两侧的风景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当宏图在握或是功败垂成的时候,才会想起在遥远的某个午后,自己也曾与谁擦肩而过,有过一瞬间的心动。只是当时忙于赶路,只是当时太过专注,只是…当时只道是寻常。
没关系,时间会教给所有人什么是失去。
也许这时,他们才能读懂听潮先生留在人间最后的只言片语:
“舍近求远,愚不可及。”